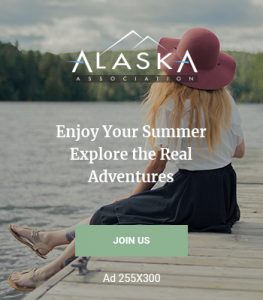北美凤凰笔会 丁鼎
作者丁鼎为理工科博士,从事科研工作;业余爱好摄影、吉它、钢
“散步与生灵”写的是在自然的边界中寻访生灵,在普通的生活中寻
在我家门口两步路的地方,就有一条沿着运河的分支小水渠修建的小路,名为“Paseo Trail”。Paseo 是西班牙语里的走路的意思,而 trail 的 字 典 解 释 是”an unpaved or a small paved road not intended for usage by motorized vehicles” ,也就是给人和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使用的小路。这条 trail 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在舒适的冬天我会沿着它跑步;而酷热的夏天到来时,我们全家就只在太阳落山时沿着它走路。
Trail 虽然大体上沿着水渠,但也有几段地方道路变得蜿蜒,离水渠之间有些距离。而这片夹缝的土地上,除了一片荒地还有一户人家 – 没错,在这里真有一户住在那里的人家。这家的院子由一面有洞的破墙和三面残破的篱笆围起来,里面的简易房屋长得有点像小号集装箱,上面架着看起来至少有 40 年历史的那种老式空调。房顶上有线从从不远处的电线杆就那么直接连了过去,我不知道生活用水是怎么解决的,但是院子有时可以看到喷灌系统的水柱,所以水应该不成问题。在慷慨的浇灌下,院子里铺满了不知名的绿油油的野草。每天路过的时候,时不时会有那种墨西哥经典的欢快歌曲从院子里传来,还有小孩子在院子里光着脚丫疯跑。这个位置独特的房子恐怕不见得合法,至少肯定不会属于市政当局的规划。但它给我一种离奇但无比真实的感受:我每次看到这个我这里罕见的、贫民窟一样的房子,都会从他们的笑脸上,看出里面的人过得很快乐。
在亚利桑那州,有 32%以上的西语(西班牙语)人口,他们应该都是从墨西哥合法或者非法地来到这里的,华人称他们是“老墨”。与之相比,亚利桑那州的亚裔只占总人口的 3%,华裔就更少了。老墨们填补着这里所有的底层劳动力需求:房屋清洁、园丁、修路、修车、建筑、搬运装卸,你能想到的所有的重体力劳动全都是他们的身影。我家的园丁已经给我家干活有十年了,每两周来一次修建草坪修剪灌木清理后院,哪怕盛夏的烈日下,也是戴着帽子披着防晒头巾汗流浃背地干活,从来也没有随着不停增长的物价而随意涨价。
虽然也许有着个例,但是很明显,老墨们普遍收入有限而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着一大堆孩子,也从来不重视子女的教育(孩子多了肯定也顾不上),哪怕孩子只要小学能毕业,就是件很值得全家开心的事情。他们做着最底层的体力活,开着破烂不堪的旧车,住着远离所有好学区的旧房,穿着二手店淘到的衣服,每天喝着可乐吃着廉价的甜食 –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镜像一样成为了华人的反面。但是以我亲眼所见,老墨总是比我见到的华人都要快乐很多。在当地人口占比如此之高的他们,却未见到他们有什么政治诉求、对平权的要求,只是时不时在公园里一大家子听着欢快的歌开心的聚餐。我倒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老墨的生活直接指明了快乐最本质的来源:不把幸福等价于更多的金钱和物质,不惧怕死亡,也不为衰老忧伤,不为过去懊悔,也不为未来忧愁,只是简单地认清当下而安居于快乐。除此之外,其它任何依附于外在形式的快乐,都如饮鸩止渴,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但我也知道,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说法,就如鸟巢禅师对白居易的原话一样 – 永远都是“三岁儿童虽懂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只要几步走过这个神奇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识的快乐人家,trail 和水渠之间便留了一片荒地。夏天的时候,这里有着干裂的土块和枯萎的草丛,但是经常能远远看到灰色的野兔在夕阳下奔跑,不知为什么只有兔子的尾巴带出一点显眼的雪白。有时候我也难免无法抗拒涉足荒原的诱惑,小心地躲开满地的地鼠洞和有点吓人的巨大蚂蚁而步入黄土和荒草中。一次我的脚步突然打扰了一个小蝗群,于是我身边的荒草丛中,突然飞起一小群黄褐色、颜色上几乎跟土地无法分辨的蚂蚱,在夕阳下向四周散去 – 这个场景让一下子让 déjàvu 这个法语词蹦到了我的心头,同时也带来一种难以言传的、非常恍惚的感受。在我小时候出生的黄土地上,眼前这个场景肯定出现过不只一次。在异国他乡,被夕阳下的蝗虫群唤起的“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听起来似乎不太有诗意;但我依然会忍不住想起艾略特《荒原》里的片段:
Over endless plains, stumbling in cracked earth Ringed by the flat horizon only
 每当冬天到来时,只要有一点点的降雨,这片荒地会在一夜之间以魔术的手法变出各种绿色的植物。虽然最常见的是扎人的风滚草,但是也会有成团成簇的野生绿苋菜一直长到齐腰高。每年冬天,我们都在这个荒地里采收着苋菜,“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用来焯水凉拌包饺子做馄饨我们总是吃得不亦乐乎。当然,市政当局并没有放任这里野草繁茂,去年居然用农业机械把荒地生生翻了一层,可怜的野苋菜被埋在下面之后就完全不见影踪了,为此我还有点沮丧。但是谁曾想,没过多久,被翻了一遍的荒地居然又冒出了全新的植物。在我再三对照仔细鉴别下,觉得就是“ 青青园中葵 ” 和“采葵持做羹”里的野葵 。 不知什么原因 , 这种曾经的“百菜之主”,在明朝后就被人们慢慢忘却而变回了野菜,在现代人的餐桌上更是罕见。汪曾祺的《人间草木》里有提到,吴其濬仔细考证了“葵”是南方称为冬苋菜的野菜(并不是苋菜)。一开始我们还只是小心翼翼地收了点嫩叶尝了尝,结果发觉这个菜分外好吃,凉拌炒菜都绝对是一把好手,尤其是用来拌肉馅,入口像极了市面上难得一见的新鲜荠菜。到后来,我去跑步的附加任务之一就是收收野葵,我们一直吃到野葵都长得有点老了,不好入口才肯罢休。
每当冬天到来时,只要有一点点的降雨,这片荒地会在一夜之间以魔术的手法变出各种绿色的植物。虽然最常见的是扎人的风滚草,但是也会有成团成簇的野生绿苋菜一直长到齐腰高。每年冬天,我们都在这个荒地里采收着苋菜,“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用来焯水凉拌包饺子做馄饨我们总是吃得不亦乐乎。当然,市政当局并没有放任这里野草繁茂,去年居然用农业机械把荒地生生翻了一层,可怜的野苋菜被埋在下面之后就完全不见影踪了,为此我还有点沮丧。但是谁曾想,没过多久,被翻了一遍的荒地居然又冒出了全新的植物。在我再三对照仔细鉴别下,觉得就是“ 青青园中葵 ” 和“采葵持做羹”里的野葵 。 不知什么原因 , 这种曾经的“百菜之主”,在明朝后就被人们慢慢忘却而变回了野菜,在现代人的餐桌上更是罕见。汪曾祺的《人间草木》里有提到,吴其濬仔细考证了“葵”是南方称为冬苋菜的野菜(并不是苋菜)。一开始我们还只是小心翼翼地收了点嫩叶尝了尝,结果发觉这个菜分外好吃,凉拌炒菜都绝对是一把好手,尤其是用来拌肉馅,入口像极了市面上难得一见的新鲜荠菜。到后来,我去跑步的附加任务之一就是收收野葵,我们一直吃到野葵都长得有点老了,不好入口才肯罢休。
如果你稍微多留意的话,很容易在一路上找到各种各样的鸟。蜂鸟、乌鸦、红雀、野鸽、啄木鸟、鹑(Quail)都其实随处可见,我们甚至见过长腿猫头鹰的身影。但是沿途能听到、叫声最独特的一定是反舌鸟(Mockingbirds,也称模仿鸟),它可以模仿非常多不同种类的鸟叫,甚至还能依靠自学,学会新的叫声。如果你刚好读过《杀死一只知更鸟》的话,这个书名其实是个误译,因为原书名是“杀死一只 反 舌 鸟 ” 而 不 是 知 更 鸟 (AmericanRobin)。但是这个错误的翻译已经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无法再较真去改过来了。
今年夏天我们见到最特别的鸟,莫过于一只双领鸻(Killdeer)妈妈。每次走过的时候,她就在路边不远的地面上呆着一动不动,哪怕走得很近看着她,她也在原地也保持不动。一开始我甚至以为她不是一只死鸟就是一只呆鸟,直到朝她走近了观察离她只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她就突然张开翅膀用尖声叫着,很努力地做出威慑的样子,而且坚决不肯离开原地。我们都意识到,她肯定是在守护自己的鸟蛋。在这之后,每次经过的时候我们都尽量不打扰到她,只有 Ryan 不肯罢手,每次经过都刻意走向前骚扰她一番,甚至有一次在她离开觅食的时候拍到了窝里的四个鸟蛋。

凤凰城整个地势平坦,四面环山。虽然也算是城市,但是至少在我家一带附近根本没有任何高楼。在没什么人的 trail 上继续往前走着,放眼望去可以一直看到远处绵延的山脉。

每当落日给大地洒满金黄的时候,如果是万里无云的时候,那么从天空到地平线会有着从蓝到橙色,有时候是从蓝到淡紫,或者是到淡玫瑰色的一种异 常 优 雅 的 渐变色 。而一旦天 空 中 有 着 足够 的 云 彩 , 那整个天空就会的色彩在那 一刻就如同打翻了漆桶一般绚烂:红、黄、橙、紫、蓝各种色调会随意涂抹着整个画布,整个水渠更是倒映着整幅画面。

那一刻的落日用豪华的手笔为最普通的景色点石成金。不过这黄金一刻通常也就 5 分钟左右,几乎是随着走路的步履转瞬即逝,然后就把整个天空丢给了深蓝和星点 – 每当这时候,也意味着该踏上回家的路了。
如果你以为这条小路就是我喜欢住在凤凰城的理由,那么你着实错了。除了北上广纽约东京那些城市化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程度的地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你都可以找到人和自然那模糊的边界。而步入这种边界的所见,也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美景,也有可能只是恐慌。这条小路上除了我之前说的蛇和指头肚大的巨大蚂蚁,也时常有半个筷子长的大蟑螂旁若无人地快步穿行;哪怕不提亚利桑那常见的剧毒黑寡妇蜘蛛、蝎子、黄蜂,我也在水渠边见过背上都是疙瘩,每个疙瘩上都是洞,让我密恐直接发作的巨大蟾蜍。平坦、空旷而酷热的凤凰城,只是用冷漠而坚定的态度,恰好把这条边界摆到了我家门口,让其实喜欢宅在家弹弹琴读读书的我,几乎是别无选择地、时不时体会着步入自然边界的感受。即使是那种已经根本看不到地平线的大都市,你也可以找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感受。
我从未觉得需要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找出一个喜爱的理由 – 在我来看,这种做法本身的动机就是荒谬的,又落入了向外寻求的错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跟依然不停在加速膨胀的整个宇宙相比,我们宛如蜉蝣的短暂生命,其实连沦为其间一粒灰尘的资格都没有。无论以何机缘,身在何处,我们能做到的不过是认清当下而已。当然,我会很高兴地用文字带你在酷暑的落日中走走这条小路,看看那神秘的快乐人家和夕阳下的水渠。大概过不了多久,那只双领鸻妈妈的四个孩子应该已经能飞上天空,朝远方四散飞去,只留下一个碎石的空巢。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